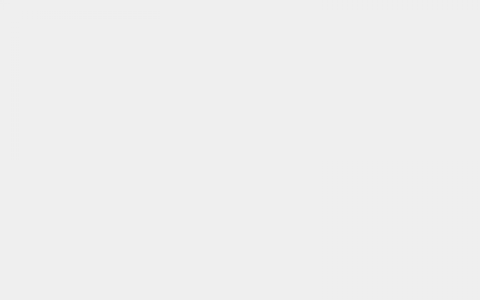一座“桥”的命运
我在新庄出现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叫桥,是我听人家叫我桥,我才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和许许多多架在河上江上、沟上渠上的名字一样,叫做“桥”。
我的身材并不高大,长也就六七十米,宽不过三米,整个的一个小窄绺。
我的身子桥的骨比较单薄,这一点,我自己心里既清楚,又明白。
我刚刚躺在河上的时候,身体两边还有十二个爪子,不是平伸的,是立起来的。爪子不高,就一米二左右。就像我的手指头,牢牢地抓住我的身子,也保护着从我身上过的人,不让他们掉下河去。
十二个爪子分布在我的身体两侧,一边六个,还挺均匀。听人们说他们把我自己戏称为的“爪子”叫做“栏杆。”叫就叫呗,叫啥都一样,反正起的功能也一样,就是防止人掉进河里。真的,只要是栏杆,就起咋用,哪怕叫猫蛋,狗蛋一样。主体功能没什么变化。
我的身子骨刚一长结实,有人就在我最东头的爪子上刻下了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我仔细琢磨这八字,真是太有意思了。
听我的老辈桥说:清朝有个县人,好像叫郑板桥,他画的竹子有一绝,如果有人保存个几百年,也就发了财了。当初他好像说过这么类似的一句话,叫什么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靠天靠地靠老子,不算是好汉。
他说这话,和后来的好汉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好像是一个概念。都提倡努力奋斗的意思。
其实,说是我老辈桥说过的话,这是我有点虚荣,假借来的。
老辈桥哪有那么大的学问,这些话是我听来的。是在庆祝我的诞生。支书在我的脚边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时说过的一翻话,我记性好,恰巧就记住了,现在拿出来卖弄卖弄。
庆祝通车那天,支书还从供销社弄来一挂鞭炮。鞭炮说是一万头的,其实,远远不够。按理说,一万头的鞭炮该有一万颗才对。
可你知道,有时候这话里头虚头比较大。要是打仗的时候,号称百万雄兵,要是我看,实际上有十万都不到,我为啥知道得这么清楚?不是有句话嘛,老辈人说,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多。
那一个个兵士就得从桥上过,从桥上过的时候,我的桥先辈们一个个数着他们哩,数过之后的信息密码不知怎么的就遗传下来了。只要我们桥一诞生,这些信息就自动在我们体内生成,永不遗忘,你说神奇不神奇。
三国时,曹操征刘备,孙权的赤壁之战,不是号称八十万吗?实际上在前线作战的只有二十万。
著名的淝水之战,前秦八十万军队南下伐晋,却被符坚说成:我百万大军,一声令下,所有士兵的鞭子投入长江,足可把江水断流,长江天险还有什么好怕的?
结果这牛皮吹大了。其实我的先辈桥还真的没想到他们这么多兵力会败给晋军区区八万人,符坚的“投鞭断流”变成了“风声鹤唳”。
说远了,说远了。还是拐回来说说咱这小河,说说那天通桥时放的鞭炮。
本来应该一万颗的鞭炮,实际上九千都不到,因为它一颗颗炸响之后,在我的身上这抓一把,那挠一把,跟挠痒痒似的,让我心里很舒服。它挠了多少下,我就数了多少下,一共是八千五百七十九下。
况且,鞭炮炸响之后,纸屑乱飞,那时的鞭炮不是用红纸裹的。为了节省纸张,体现艰苦奋斗,俭省节约的精神,往往是从造纸厂收购的废旧纸张中挑些好的,运到鞭炮厂,再由工人用手裹成。
按说裹炮这活儿可真危险,也真挣钱。
真是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挣钱,中国有句老话:风险与利益同在。
但是炮厂爆炸起来也真吓人。
那次,听我一个远方的桥叔说,他们那儿的桥边有个炮厂炸了,四百二十间厂房有四十间全部炸平了,幸亏里面正在工作的人员少,但也有几个被炸得找不着人了,只剩下些碎皮烂肉。
虽说炮厂老板赔得多,但他的家人花着这钱的时候,心里也一样不好受啊,毕竟这真的是血汗钱哪。
我是怎么拥有这么大的信息量?
从我身下流过的水里有水草,更有各个地方的鱼鳖虾蟹。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我这桥墩下就像一个大茶馆,况且桥墩下有时也聚集些水草,水草就像人类的房子,人走累了也想找个旅店歇息一下,何况是鱼呢?
物人相通,鱼也一样。他们在我身子底下歇息,侃天。他们用嘴说,我用耳朵听。侃着侃着我就知道了天南地北的事。
禽有禽言,兽有兽语,我们与人没法沟通,可我们之间是有共同语言的,不是说万物有灵吗?
我也一样,他们说,我听,有时也插上一两句话,说的多了,我也就记住了。要不,我咋知道这么多?
一晃三四十年过去了,我经历的事,见过的人,听过的话也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有时候我真想抽空写个回忆录。可回忆录好写,又有谁看呢!写好之后,说不定哪个后生小辈又嘲笑道:“又搬弄些老掉牙的东西来浪费我们的时间,谁看呢?有空不如去迪厅转转,出出汗。回来洗个澡,睡个好觉,多好。”
想了又想,最后还是摇了摇头,一代有一代的事,我自己管好自己就行了,说多了净惹人烦,做好自己,做好自己。我告诫了自己两次。
不过,我挺喜欢与比自己年长的桥说话,从他们身上汲取经验,省得自己多走弯路,可是有些事我主观上避免得了,有些事我想避免也当不了家了,因为那已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我不是只有三米宽?当时建成的时候还没有人说啥,因为那时过的是自行车、架子车,或者赶个小毛驴,拉个架子车从我身上驶过已是不得了的事啦。
我是比较喜欢听那小毛驴得得地从我身上踩过,敲的我的心脏一跳一跳的,特舒服。时间长了,我还知道毛驴主人分别给它们起的名字:那个一身黑的叫黑皮,后屁股上长了黄毛的叫赖蛋,脖子上有一圈棕毛的叫项圈……
除了知道它的名字,我还知道它们的习性,那个黑皮每次走到我身上,总喜欢在我的第二个爪子边蹭痒;那个赖蛋总是边走边把屎屙在我的第四个爪子边,那个项圈总喜欢在我的脚边撒尿……
它们好像形成了条件反射,一到我这儿就欢喜得不得了,不给我留点纪念是不肯离开的。
好像从什么时候起,我的这些披毛带甲的朋友渐渐不见了。我知道,它们一个个先我而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心里有一丝丝悲哀,我知道,毛驴正常情况下可以活20年,以人的寿命来计算差不多百多岁了。况且毛驴朋友今天拉柴,明天运砖,后天出远门走亲戚,没一天闲着,出了大力,干了重活儿,能活够20年的还真不多。
尤其是还些年驴肉贵,说实话也不怨驴肉贵,就怨人炒作炒的了,说什么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那真叫一个鲜。
说这话的人也不动脑筋想想,你啥时候见过龙肉了?龙是十二生肖里的属相不假,可十二生肖中有十一种都是地球上实实在在的生物,是现在我们肉眼可见,手可触摸的。龙,谁见过?
有人就不高兴了,现在没见过,远古之时难道就不存在了吗?兴许以前存在过,后来又灭绝了呢?譬如恐龙。谁见过活的,西峡不照样挖掘出来,还建了个恐龙博物馆吗?不但有恐龙化石,还有恐龙蛋化石呢,还足以证明恐龙是卵生的。
不但这样说,还拿出一张泛黄的报纸,那上面赫然有:1934年7月初,很多人在营口田庄台上游发现一条活龙,人们用苇席给它搭凉栅,挑水浇,寺庙僧侣每天为它作法超度。数日一场暴雨过后,它消失了。这话说的人,振振有辞。
说到底,真有龙了,龙就站在你跟前了,你也不敢拿刀子削下一块肉填进嘴里,光是野生动物保护法就让人心生敬畏。说不定,还像对待全世界仅存的两头非洲白犀牛一样,有人24小时持抢保卫。这待遇,估计一般人也享受不到。
说白了,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说法不过是为了吃驴肉找个美好的借口罢了。
想想,驴也真够可悲的,干了一辈子活儿,受了一辈子罪,到末了,还被剥皮抽筋,剜肉剔骨,敲骨吸髓。
想想就心寒,我替驴朋友心寒。
驴朋友拉的车没了,辗过我的是那三个大轮子的蓝色的时风车。
这车马力大,轮子高,下田有劲儿,拉个土,拉个粮食啥的不费劲。
农村能人多,有时候几个人一商量,换个加大轮,开起来能撵火车。当然,这是他们在我身边吹牛皮的时候我听说的。
一换时风车,他们就不能像以前那样赶着驴车,二车一相错,在桥中间说话了,因为我的身子窄呀。
要是两辆车同时在桥两头出现,只好一个一个的过。一辆先退到人家地里,等一方过去了,另一辆再驶上主路,再过桥。
以前从我身上碾过的石磙,打麦用的圆滚滚的那种,还有磨面用的石磨,一个一个被城里来的人收走,四十块钱一个,说是建什么民俗博物馆,让后代的孩子们看看农耕文化。
要是饭店的来收磨盘,那价格就高多了。少一百不卖,他们给钱也爽块,不搞价线,一掏就是一张红票。
我细心听饭店的老板要磨盘干啥。原来是放在饭店旁,专为装饰用,吸引食客们怀旧,老人怀旧,小孩子看新鲜,来吃饭的人多了,老板自然就赚得多了。你看这做生意的多不容易,还得绞尽脑汁想办法。
不过,要从我们桥的眼光看,可能我的眼光有点老,但也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关键是菜的质量要站住脚,大厨水平要高。
现在的人吃饭门精,饭菜一搭嘴,就知道行不行,也决定了下次来不来。
除了收磨盘,我还见以前庄里的老爷爷老奶奶们买过的斗啊、大秤啊、礼盒呀,一件件被装上车,听说都运到了博物馆里。
也对,现在打面都用打面机了。收麦子有收麦机,一遍过去,就差在地里边打出白面来了。不过麦子得淘洗,要是在地上直接打出来,里面有粘土、沙粒啥的,吃的时候会咯牙的。
收棉花机、收番茄机、收枣子机……这些机器一上,以往的石槽、石磨统统退位。效率高了,人工省了,再也不像以前收麦那样,一连准备了好多天,全家老少齐上阵累了个半死。男人男人,就是在田地里下力气的人。看来,这个观念已经跟不上时代,不改不行了。
男人一解放出来,就要出去打工了。
到大城市去,到北上广深去,到……去,实际上,哪儿能挣钱往哪儿去。
以往吃过晚饭,夏天的夜晚,经常在我身子骨边侃天的小伙子早已变成了六七十岁的老人,当年撒欢遛圈的小孩子长成了青年,已有好些年没回来了。
听他们的长辈说,这个在江苏安了家,那儿工作好找;那个在新疆定了居,国家移民有政策,优惠大;那个在深圳买了房,因为去的早,一套房子就值千万,要是卖掉回来置业,能抵上半个庄子……
那几天听得我耳朵嗡嗡的响,心里痒痒的。要是我能动,我也早飞去了,外面遍地黄金,好像在那儿一弯腰就能拾个千儿百八十万的。
我不能动,我还得坚守自己的岗位。
可是我的手,也就是那一道道栏杆,还有我的一根肋骨—一块桥板全部受到了伤害。
话还得从杨树身上说起。说杨树还得说板厂。
这些年社会发展得很快,这一点大家都有目共睹,真可以用一日千里,日新月异这些词来形容。
发展一快,楼就建多了,建高了。楼一建好,里面不能总是个空壳子,就需要家俱,打家俱除了用玻璃、钢材、铝材之外,用得最多的就是木材了。
过去使用最多的木材是桐木板,因为桐木板轻,成材快,又不易被虫蛀,耐用。后来,不知从哪儿引进了一种速生杨树,它长得就是快,人家说十年树木,那是一般规律,这十年的时间用在杨树身上,虽然时间相同,可成的材的量绝对不一样,它一棵顶其它两三棵树的木材量。
世人喜欢啥?钱。恨不得今天栽下去明天就长成参天大树,迅速地换来钱,装进自己兜里。对树是这样,对其他动物也是这样。速生鸡、速生鸭,速生猪不都如此?
如果猪蹄子卖得好,最大的愿望就是猪身上全是蹄子,那才遂了愿。看见蹄子眼睛都冒绿光,泛出莹莹宝石来。
现在种的杨树也是如此,长得慢的树种靠边稍息。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全都种上了这种速生杨。
速生杨长得可真是快,窜得又高。树干能剥板,树枝能剥板,剥了板之后余下的芯还可作木锨把,细枝嫩条打成粉沫又成了造压缩板的绝好材料。
压缩板真是好,本来是废弃的东西,加上粘胶,就成了又厚又重的板,抬起来沉,造成老板桌,老板椅之后,往那空荡荡的房间里一放,特别上档次,赚的钱老鼻子多了。
速生杨最大的优点就是产材量大。缺点也有,每到春天,杨绵就乱飞,铺天盖地的,把人粘得都戴上了口罩,否则,简直无法出门。
特别是患了鼻炎的人,喷嚏一个接一个。路边的草丛里像是《西游记》里蜘蛛精喷吐的蛛丝网,把人牢牢地粘了进去。
拉树的车是那加大轮的时风车,三个轮,要多有劲儿有多有劲,拉个三层二十一根树干,简直一点劲儿不费。
车不费劲儿,可我受不了。我那身子骨又单薄又细弱,拉树的车一上来,才走十多米,刚到我的脚脖子,车右轮下的我的一根肋骨就断了,栽进了河里。
自然而然地,时风车上的杨树干就像下饺子一样往河里跳。
我眼睁睁地看到坐在司机篓里的那对小夫妻吓得腿发软,脸色煞白。
开始我还为他们担心,后来很快释然了,拉树的车一般不单干,单干这活儿也接不了。
后边的车陆续赶了上来,一看这架势,有人迅速地把小夫妻拉下了车。
我的肋骨断了。车陷了,木头掉进河里了。这是多少年才会出现的一件大事。庄里头的老老少少几乎全出动了,简真比看大戏还热闹。领车的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又精又壮,一双眼睛像铜铃,精光四射。
他几乎在三两分钟间就拿出了主意。
“来保,你们三个先把车上的木头卸下来。”
“运旺,你的车掉转头,绕小路进庄,带上钢索,停在桥东头,拉车。”
“谷澳,你们三个下到河里,用钢索,大绳分别捆住桥板的两头,再把绳头交给运旺他们。”
……
领车的一双眼冷峻、深沉得像要拧出水来。
几个年轻人如同蜂巢里的工蚊,一齐忙碌起来。
我的头边脚下头被堵住的车辆主人们也下了车,站在一边指指点点,看着热闹。
“多长时间能弄好?”一辆挂着外地牌照车的主人问。
“很快,也就两个多小时。”领班的头也不扭。
我看见被陷车上边的木头被卸了下来,压在了我的腰上。
被陷的车被运旺的车拉上了桥面。
被卸下的木头又被重新装上了车。
来旺的车倒了回去。
被陷的车带着木头开出了我的额头。
运旺的车又开了回来,扯上了谷澳递上来的钢索。
我觉得我的那跟肋骨两头都被钢索缠得结结实实。我挣了挣,挣不动。只是觉得肋骨两头被细钢筋拉扯住的如同人的筋骨肉丝相连的部位有点疼,但疼得舒服。
“准备好了吗?”领班看着他们缠好了绳索,往两边稍微闪了闪,大声问。
“起。”领班用力挥了一下手,就像解放战争中的一挥手下了总攻令,万炮齐鸣。
桥两头的时风车就叫起了劲儿:“突突突……”
河并不深,也就一米多一点,不到两米。因是夏天,几个人干了一天活儿,正好跳进水里洗个凉水澡。
领班的手里掂着个木棍,在我的肋骨吊起来复位的时候把木棍轻轻地伸进缝隙里,顺着一撬,我的那根肋骨就如以前一样,稳稳地嵌在了我的腰里。
我觉得如同练气功的人被打通了任督二脉,全身气血贯通,整个身体一下子通畅起来。
人群里响起了一阵阵掌声。
桥,又通了。
不过我的那些手——栏杆有几只没了,是被树干撞下河去的。
我也真疼,可我没办法,我的手也没招谁也没惹谁,可我不能动,只能任人催残。
再后来,就是风刮日晒雨淋,我的那些手又细又弱,底座下的凹槽有了松动,越松动又越有人晃,晃得我的神经一阵阵抽着疼。
三晃两不晃,晃着晃着就把我的一只又一只手晃掉了。全都扔进了河里。
当然,都没有人下河捞上来。因为那天我的一只手被晃掉推进河里的时候,有人说捞上来吧,有人接口道:“捞它干啥?捞上来也安不上了,还会掉。谁要不知道,往上边一靠,想歇会儿,不就掉进河里了?净害人!”
时间不长,我的一双双手就全没有了,整个身体两则光秃秃的了。
整个桥面——也就是肚皮上高高低低,凸凹不平,当然只有人使用没有人维修,哪怕用铁锹铲点土垫垫也好啊。
这种情况不妙,肯定可能要有点啥事发生。我也说不准。所以先用肯定后用可能。但我不知道事件会从哪方来,又会发生多大的事。
直到那一天。
那天是个阴天,整个天空阴沉沉的,要下雨了,我仰脸看着云,云低头看着我。
远远的,从庄里过来了一个人,骑着电车。
电车骑得并不快,我看到是一个女子,年龄并不大,也就二三十岁的年纪。
“可别颠到河里了。”我听到她的心跳声。
怕啥就有啥,说不了是谶语或是经验。
她骑车竟然骑到了我的身体最边沿,最边沿长着茅草,把桥边完全遮住了。桥边又有个小坑,她的车轮一颠,一上一下,双手就有些松动,车轮一偏,她的身体就在一秒钟之内向桥下倾倒,她连一声“唉”都来不及喊就掉进了河里。
我这才看清,她还怀着身孕。
如果有人掉进了河里,文人会说:她如同一只翻飞的蝴蝶在秋天里,在秋色里,翩然飞落,落进秋的暮色里。
这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说的话。他们有事没事,喜欢喝着酒,品着茶,拈着笔,说一些不酸不甜不咸不淡的文字。我不行,我要做事,说话往往直捣黄龙府,一语中的。我只知道人掉进了河里,得救。尤其是一身两命的孕妇。
可是我动也动不了,喊也喊不出,干着急,摇晃了下身子,扑籁籁的掉下了一些灰尘粒。
还好,正在河边桥下钓鱼的几个人看见了,几乎同时扔下手中的鱼竿,飞奔到孕妇落水的地方,一个一个跳进了水里。
值得庆幸的是,孕妇掉进去后并没有下沉。更万幸的是,随着他一同掉下去的那辆电动车还算有良心,没有砸在孕妇的身上,万一砸上了,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几个人连拖带拽把孕妇弄上了岸,还得小心她肚子里的孩子。惊魂甫定的孕妇喘了一口气,上岸后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给几个救她的人磕头,一个又一个。
这下倒弄得几个人过意不去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现在是一身两命,胜造七级浮屠了。还得帮帮她。
也没人商量,几个人又一齐下了河,两个人抓前轮,两个抬后轮,深一脚浅一脚把那辆电车又弄上了岸。
“这车真沉。”
“淤泥也深。”
“不知道电瓶进水没有,进了水就不能骑了。”几个边抬边说。顺手又抹了一把脸,因为手上有淤泥,把脸上抹得黑一道黑一道的。
我想笑,可我笑不出来,只好憋在肚里。
孕妇回过了神,掏出手机,她的手机是防水的,揣在裤兜里,她的裤兜外有个拉链,拉住了口,也没掉进水里。
要拨电话,可她的手指抖抖地不听使唤,怎么也按不准键,“我来帮你打吧。”一个钓鱼人说。电话通了,是她丈夫接的。
电话接通的刹那,小媳妇哭得是个痛快,唏哩哗啦的。
她的丈夫第一时间赶到了,同时赶到的还有一车人,听她们叽叽喳喳地说,我才知道这里面有她的婆婆、公公,她的邻居、她的叔叔。
正好够一车。
“啥也别说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她婆婆说。
“救了咱命,咱得好好感谢。走,我请客。”她丈夫说。
几个钓鱼人忙不迭地收拾好了渔具,一齐来到了聚贤庄酒楼。
那一晚,小媳妇的丈夫嘴皮子磨得又光又亮,说得最多的就是两个字:感谢。
当然,聚贤庄我没去,也去不了。酒宴上的一切是听那几个钓鱼人说的。他们后来又来到这儿钓鱼,闲侃着侃到了那天救人的事。
末了还说,估计那媳妇也该搁下了吧。
要是到月了,也快了,这孩子长大了保准是个有福的料儿,不当大官就得发大财。
没过多长时间,那掉下河又被救上来的小媳妇果真带着她的孩子过来了,那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真是可爱。
只不过,他还不会说话,只是用一双大眼睛骨碌碌的瞅着她娘当初掉下去的地方。
这事发生不久,又发生了一起一个骑三轮车的老婆婆掉下河的事件。
一传十,十传百,接连有人掉进河里的事越传越远,终于传到了领导耳朵里。
领导来了,可他的车不敢上桥。
因为我的又一根肋骨那天晚上被一辆小型吊机压断了,因为天黑,我没来得及看清是谁。它是前带过去了,后带一卧,硬生生地把我的肋骨卧断的。
我的肚皮上满是窟窿眼儿。有的地方只剩下肚皮贴着脊梁骨了。
领导上了桥,站在了我的肚脐眼上,前看后看,左看右看,看了足足有三分钟。
“打个报告吧。”领导对跟在屁股后边的支书说。
支书的头点得像鸡叨米。
我知道,我就要没了。
没了也好,我不怕死。就怕半死不活的躺在那儿活受罪,今天断了手,明天折了腿,大后天又折断了脊梁骨,那简直比杀我还难受。
我最希望的死法是咔嘣一声响,断成两截,一命呜呼。最不希望的是半死不活,不死不活的活受罪。
炸药塞在我的腿上的时候,我不感到悲衰,相反还感到高兴,是该走的时候了,一切都结束了。
再见,我的鱼鳖虾蟹朋友们。
再见,我的水草树丛伴侣们。
“点火”,随着一声有力的呼喊,我在一阵爆炸声中变成了粉沫。
我在半空中冉冉升起。我知道,用不了一年半载,一座新的桥梁会在这地方重新建起,它将肩负起我今天的责任与使命。一阵风来,把我的肉体吹得飘散到了远方。
一结都结束了。
2019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