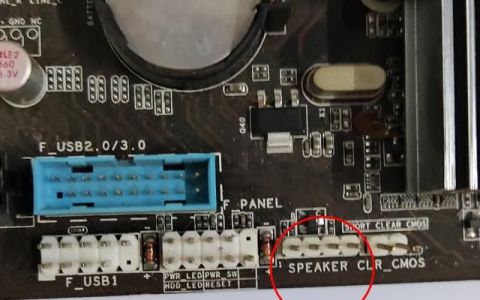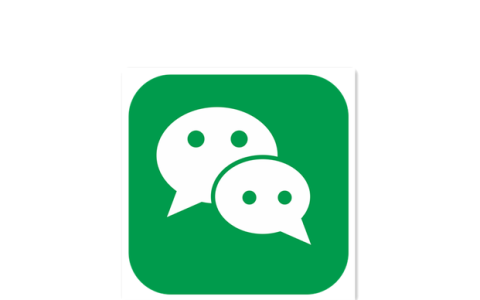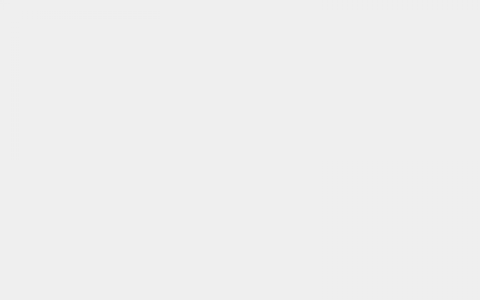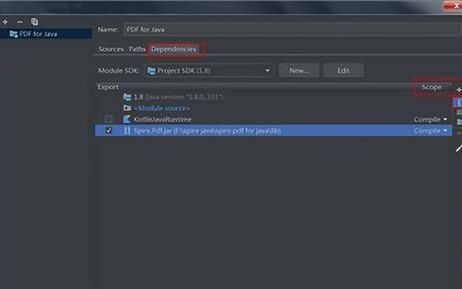捕麻雀
李直
麻雀是白沙梁最常见的飞鸟,数量极多。尽管一年四季都有人捕捉它们,感觉从不见稀,似乎越捉越多。
孩儿们捉麻雀,都是人扛人——也叫搭肩,即一个人踩在另一个人的肩上站成人梯,去房檐下掏,从未操练过别的方式。那天,听老村长吹牛“在歪脖柳上抓”,便觉得新奇,缠磨着他传授一二。
“那时我年岁小,和你们一样大,刚当上村长没几天,时常去老沈家。老沈家那时住老院子,八十多亩,三进三出的院儿,大门洞子就抵咱们三间屋。我爹是车老板子,是个好把式,给老沈家赶大车。那大车,四匹大马拉着,好大。但人家门洞子也大,大车能从大门洞子直接跑进去。”
老村长的话,总是从吹牛开始。
“那年,我当了村长了,就天天去老沈家了,天天在那儿混吃喝。人家是大地主,良田千顷,牛马成群,三天两头就杀一口大肥猪,鸡鸭更是家常便饭。我能在那儿吃,因为我是村长……”
老村长说话,十句有九句离不开“村长”。
“老沈家有四个小少爷,现在还都活着呢,就是沈鸿喜沈鸿禄沈鸿福沈鸿寿,他们和我差不多大。他们求我抓个家雀儿给他们玩。我爬上柳歪脖子就抓了十来个。”
我们满腹狐疑地盯紧了老村长。
“咋的,不信?不信可不行啊。那歪脖子柳,是棵老树,三四个人手拉手才能环过来。好几百年了,老沈家还没到白沙梁呢,它就在那儿了。盖房子时把它圈在里边的。那时,咱白沙梁的家雀儿,比现在多,多出不少,上了树就抓。”
此时,我们中有人打断了他的信口开河:
“那家雀儿都是带翅儿的,看见你就飞了,你咋抓?”
老村长眨了眨眼,思谋了一会儿,皱了皱眉,回忆了一番,似乎方才想到麻雀是生有翅膀的会飞的动物,不是伸手就能抓到的。但马上,他又信心满满地说:
“忘了告诉你们了,树上,挂着鸟窝呢,有木板子钉的,有柳条子编的,绑在树杈子上。老家贼不知道内中有计谋,以为是自己的窝儿,吐噜,就钻进去了。它在里边还啥都不知道呢,我就上去了,凑近了,手一伸,嘿,就逮住一个。”
我们听明白了,老村长之所以能上树逮麻雀,是因为挂了鸟窝。我们当下就决定,回家做个鸟窝,然后就能像老村长一样上树逮雀了。
做鸟窝是个技术活儿,用料上还有要求,不是木板就是柳条。于是,家里有木板的,就用木板钉,没有木板的,就用柳条编。那天晚上,白沙梁这个小村子里,许多人家都灯火通明,都有个孩儿在专心致志的挑灯夜战。
驴子他爹是木匠,家里闲着好多块木板,有大的也有小的。他当然就用木板钉了。他先是求他爹给他做个现成的,没想到除了挨一脚外,还外搭了一句骂:实在闲,就挠墙根去。没办法,驴子只好自已动手。他动用了他爹的锯子和斧头,丁丁当当的钉了个长方形木盒子,还挖了个拳头大小的孔洞。
枝子家即没木板也没柳条,她别出心裁的用谷秸编了一个鸟窝。金黄色的一个尖顶圆柱类似粮仓的东西,也掏了一个洞。散着淡淡的草香。
更多的人,都是用柳条子编的鸟窝。因为我们白沙梁柳树极多,哪家院子里都有几棵,柳条想用多少就折多少。但编出来的鸟窝,却形状各异,有方的有圆的,也有不成形状的。
第二天,是我们挂鸟窝的日子。这天,该是白沙梁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盛夏,晴朗,无风,明亮,空气澄澈且带点儿淡淡的清香。我们一行十六七个孩儿,各带着亲手制作的形状各异的鸟窝,说说笑笑的出村向西,直奔榆树林子。
老村长跟在我们身后。
他边走边抽烟边说这样的话:“嗯,看你们做的这窝儿,不大结实,是吧。家雀儿,老家贼,也挺有劲儿呢,别看它那爪子不大,也细瘦,一蹬一踹的,不是一般的力量呢。那翅,别看只有巴掌大,扑拉起来,也是个挺大的力量。”他这么说着,走近我们中的哪一个,挨着个的评头品足,什么柳条子太细,什么木板上的钉子太短,还有鸟窝洞口太小,小麻雀还能进得去,老家贼怕是得费点事儿。等等等等。言外之意是,比鸟儿们搭的窝儿,还差一些。
我们倒不觉得自己的“作品”不行,我们只觉得老村长说得离谱。难道我们忙忙碌碌了大半夜,还不及一只鸟儿的活儿?
可老村长说,我们手里的那件东西,还真的不抵老鸹窝,也不及喜鹊窝。别看它们的窝只是一堆乱草,但结实,风吹不掉,雨浇不透,是上好的房子呢。
“你们做的这些东西,经不得风,过不得雨,过不了几天,就得散架。”这是老村长的话。
我们管不得这些,我们一心想抓几只老家贼。嘴巴上说这是个鸟窝,实际上应该算是个陷阱。
进了榆树林子,马上就有人上树了。他们嘴上叼着鸟窝,腰上缠着绳子,猴子似的爬上去。尽管老村长不停的喊“不用挂那么高,不用到树梢”,但我们,尤其喜欢上树还爱逞能显摆的那几个,还是把鸟窝儿挂到了极高的地方,几乎和老鸹窝差不多的高处。我们心里自有盘算:高处,才能引来飞得高的麻雀。
我们等在树上,守侯在离鸟窝极近的地方,想亲眼看见麻雀钻进去,更想一下子就逮住它们。可是,与我们的预料相反,直到我们眼睛酸涩两臂无力,也没见有鸟儿进窝。
“哪有那么傻的老家贼,”老村长说,“老家贼,精,比人都精。它们不会轻易见窝就钻的。它们得打量,得观看,那得用去好几天呢。”
实际上,鸟儿们真的很聪明,至少其聪明劲儿,不比人类差。第二天,我们再次爬上树,在离鸟窝一臂之遥处守着,眼巴巴的盯着,等了好长时间,未见一只麻雀进去,当然也没见它们出来。它们对突然出现的新居所,抱着十二万分的警惕。没办法,我们只好从树上溜下来,站在树下,在离鸟窝很远的地方观察。好久好久,方才见到有一只半只的鸟儿接近这些新窝儿。其中大多是麻雀,也有极少的山雀。它们在离鸟窝很近的地方悬停住,忽啦啦的扇着翅膀,像一架直升飞机。我们料想,它们的眼睛,一定在细细的打量。瞧看了一段时间,还是飞走了。好像它们知道这是个陷阱似的。
后来,我们一连多日到榆树林子去,当然见到了麻雀进窝,但没等我们靠近,它们就“腾”的一下出窝飞走了。我们始终未能自这样的鸟窝里逮到麻雀。因此我们对老村长的那番在柳歪脖子上逮麻雀的经历,颇为怀疑。
有一天,老村长特意叫来了沈家的四个老头。他要他们做证。
沈家的四个老头儿,我们常见。他们住在村子西头,当然是各住自己的家里,四户老沈家,连着的四个庄稼院儿,左右只隔一道墙。
我们分不清哪个是沈鸿喜哪个是沈鸿寿,我们一律称之为老沈头。实际上他们老哥儿四个长相差异很大,可我们却觉得,人如果老了,老到一定程度上,长相几乎没有差异。甚至,四个老沈头和老村长,也十分相像。
四个老沈头站成一排,老村长站在他们对面,我们站在老村长身后。如此一来,他们四个就落入了目光的海洋里。
“你们说,我当年,在柳歪脖子上,是不是逮了老家贼?”老村长问。
“我可是给了你烧饼的。”其中一个老沈头说。
“我也给了,我把新袜子给你了。”另一个老沈头说。
“我没问你们这个,我问你们,是不是我抓住了家雀?”老村长有点生气了。
“可我给了你东西呀,哪回,你抓的那家雀,哪回都换了不少东西。”一个老沈头说。他还比划了一下,是个方形的东西,应该是块饼干吧。
“我说你们老糊涂了不是,”老村长有点生气也有点着急,他上前一步,点了一下其中一个老沈头的脑门,“沈鸿寿,你说说,你见没见着我上树,抓家雀儿,抓着了,见没见过。”
这个老沈头叫沈鸿寿,他是四个老沈头里最枯瘦的一个。比老村长还瘦,像一节朽木。他眨了眨眼睛,说,“村长,你哪回给我家雀,我都给你好吃的,月饼,糖瓜,年糕,还有冰糖,我都给过你。”
“我说你们几个是咋回事儿,你们上过洋学堂,喝过洋墨水,识文断字,能写能画,咋就听不懂话呢,”老村长再次上前一步,把另一个老沈头从一排四人中拉出来,等于向前一步走,说,“沈鸿喜,你说说,我是不是抓住过家雀,在柳歪脖子上?”
在这个沈鸿喜努力回忆的当儿,老村长又把另外两个也拉扯了一下,扰得他们晃了几晃,差点跌倒。这个动作,让四个老沈头全都瞪眼皱眉,似乎进入了回忆之中。
“逮住过。”
“是,就在柳歪脖子上,逮住好几个呢。”
经过另两个老沈头的证实,我们对老村长上树抓麻雀的事,总算有了点信服,但仍存有狐疑。从老村长那气急败坏的态度上看,有点屈打成招的意思。可接下来的场景,就令我们分外诧异了。
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极短的几分钟里,这四个行将就木的老人,竟同时充斥了活力,就像老树发芽,更像即将熄灭的灯火添了新油。他们瞬间活跃起来。他们开始回忆几十年前逝去的时光,他们争先恐后的讲述那些埋在灰尘里的过去。
他们五个人————四个老沈头和老村长,飞快的挪移了位置,混成一群而不再是刚才的那一排。动作敏捷迅疾,一改之前的迟缓滞重和虚弱无力,似乎刹那间由羸弱的老马变成了血气方刚的小马驹。
“我记着呢,”老沈头之一说,“那天,你先上树挂鸟窝,木头板子钉的,这么大,和梳头匣子似的。我还说,手真巧,真有本事,想啥来啥,刚说要上树捉家雀儿,就钉好了这么个东西。你嘴叼着木匣子就爬上了歪脖子柳。我和大哥说,村长的牙咋那么有劲儿呢,那么沉的匣子,他竟能咬住。我二哥说————”
说到这儿,他盯着身边的另一个老沈头,看了一会儿,似乎在提醒他注意听,然后说,“二哥,你说句啥话来着——”
“我说句啥话——”那个被称为“二哥”的老沈头,略略迟疑了一下,似在回忆,又似有难言之处,“我也忘了。”
另一个老沈头说,“小三问你,你就直说呗,你那话,我,小三,大哥,都听见了,也都记着呢。那天是八月十三,早上,刚吃完饭,你当时是咋说的,你就该咋说。”
这回,我们大致能区分出他们哪个是哪个了。站在最东边的老沈头,是大哥,站在他对面的是老二,说话最积极最主动的,是三儿,他站在二哥对面,另一个,是老四。但是,不多一会儿,四个老沈头就挪移了位置,我们又分辨不出哪个是哪个了。
但我们现在还是能分辨出来被逼着必说真话的那个,是“二哥”。他被逼视着,目光迷离,嘴唇嗫嚅,闪烁其辞。很显然,他不想供认但又不得不供认,只得负隅抵抗。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场景,沈家的亲兄弟四个内部分裂并开始火拼。在咄咄的逼视中,“二哥”只好低声供认,“我是这么说的,我说村长那牙,和狼牙差不多,啥都叼得动。”
“你这是骂我——”老村长怒视着沈家老二,“你咋骂人呢,我上树给你抓家雀,你在树下骂我,你这个————”
没等老村长说完,老沈头中的一个就开口劝解道:“村长啊,别生气嘛,二哥那话是不大中听,可他给你的东西好啊。月饼,他给了你一个月饼,对不对。白糖馅儿,那可是上好的白糖啊,甘蔗榨的,沙甜沙甜的,里面还夹着青丝蜜饯呢,还有瓜籽仁花生仁呢,这个,你肯定记着。”
老村长眨了眨眼,说:“记着呢。”
“那你就别责怪老二了,”又一个老沈头说,“再说,他是对着我们几个说的,没让你听见,也算不上骂你。那天,你上树,那叫快,噌噌噌,就窜上了树顶。柳歪脖子上有个老鸹窝,斗大的,住着五六只黑老鸹子,你一上,就把它们惊飞了,它们还以为你要拆窝呢。殊不知你是去挂鸟窝的。那天,你就像个马猴,顶顶机灵的马猴。”
四个老沈头争先恐后地详细描摹老村长爬树的状貌,他们不愧是读过洋书、进过洋学堂、喝过洋墨水的,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和我们白沙梁的老百姓有着天壤之别。
“你那树爬的,有水平,一看就是个身手不凡的人,”四个老沈头中的一个说,“噌噌噌,和飞似的,从主干爬上了一个树膀子,最粗的那个膀子,也就是歪脖子柳的那个歪脖子,像飞上去似的。那个鸟窝,也就是你钉的木头匣子,挂在你的下巴上,和宝匣子似的。我们几个都仰着脖子看你。咱家里的好多人,也都跑来看。我还听见有人说,看,‘郝大车’的儿子上树了。”
我们问“郝大车”是谁,老村长笑了,格外得意的告诉我们,“郝大车”是他父亲,在老沈家赶了一辈子马车。“举着大鞭,赶着骡马,那叫威风。”老村长大声的炫耀。
老沈头们说,老村长那天出尽了风头。他把鸟窝挂上树梢,就在另一根粗树杈子上趴下。这回,不像马猴了,像只小松鼠。我们白沙梁人,给松鼠取了个俗名,叫“花狸棒子”。老沈头们说,伏在枝叶间的老村长,悄无声息,不动声色,像只训练有素的猎犬。尤其那个在日本军校留学过的老沈头说,像个精干的特种兵,不加细,根本不知道树上有人。
“过了好半天,你慢慢的接近了鸟窝,”其中一个老沈头说,“你把身子拉长了,手脚也伸长了,树下的人看你,不再像人,像只大鸟,和大雁似的,和老鹰似的,根本不是人了,真的不像人。你凑近鸟窝,伸进手去,抓出了一个————”
“给了我,”那个被称为“二哥”的老沈头说,“你从树上下来,从裤子里掏出一只麻雀。眼睛是黑的,脚爪是黑的,嘴巴也是黑的,一看就是个老家贼,不是小麻雀呀。它那叫精神呀,抖抖擞擞,要是撒开了它,不知飞多快飞多高呢。你把麻雀给我了,我把月饼给你了。”
“月饼,知道不,月饼,吃过吗?”老村长问我们。
“吃过”,我们回答。但声音并不响亮,明显的底气不足,也不是所有的人异口同声,似乎只有少数几个回应了。
“啥滋味?”老村长又问。
这回,几乎没人应声。说真话,我们吃过月饼,每年八月十五中秋节都能吃到,只是少得可怜。有的年份,能吃到半块,有的年份,只能吃到半块的半块甚至更小,那么一丁丁,张嘴下肚,啥味道,早就忘了。
“不知道吧,”老村长又笑了,说:“一闻,就香,那香,烈,拱你一个跟头。我听说,老沈家的月饼,和面都不用水,用油。油和白面,孩子们,再烤熟了,那该有多香?不香死人才怪。你们谁,闻过那香味儿?”
我们十六七个孩子面面相觑,不敢应声。却涎水肆溢。
“你们呢,”老村长转向四个老沈头,“你们肯定闻过,你们是大地主的小少爷,月饼是你们老沈家烤的,肯定是知道的。那,我问你们,有多少年没闻那月饼的香味了?”
四个老沈头扳着指头计算了半天,小声的报出一个数字,而后,他们中的一个低声说:“自从来了‘大风暴’,土地,没了,房屋,没了,车马牛羊,都没了,连衣裳鞋袜,都没收了。那样的月饼,就没再吃过。”
有一小会儿,老村长和老沈头们,脸上的神情,都现出了几分凄楚几分萧然,似乎都为那没再品尝过的月饼而万分遗憾。他们那苍老的如同枯井般的眼睛里,显出一种死灰模样的光,沉寂而苍凉。
过了一小会儿,也许有好半天,他们复又活跃起来。这次复苏是由老村长引来的。
“你们几个,”他用右手中指————那是一根粗糙黝黑的手指,一一点过四个老沈头的脑门,“得了家雀,那叫一个乐呀。我逮了老家贼,先给谁后给谁,给谁不给谁,我心里自有盘算,你们知道我是咋盘算的吗?”
老沈头们摇头,都说不知道。“我知道你们不知道。咱白沙梁有句土话,那是咋说的,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心里的计谋,你们咋会知道呢。根本不知道。我在给之前,先看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哪个拿的东西好,我就先给谁,哪个两手空着,我就不给他。有一回————”
说到这里,老村长的话被一个老沈头拦腰截断了,“啊,我想起来了。有一回,你逮了好几只老家贼,你就这样————”
他边说边做出一种状貌,那是我们白沙梁的孩儿们从未见过的一种模样。他弯下腰,尽力伸长右臂,似在裤腿里边寻摸什么。其间表情不断变化,其细腻纷繁,令人惊叹。只见他皱眉、闭眼、咧嘴、咬牙,伴以深思、寻觅、为难和发狠等内心活动。这个过程相当漫长,极其逼真,仿佛真有几只鸟儿在他的裤腿子里飞窜似的。许久以后,他长长的喘出一口气,将半握着的右拳举起来,举给老村长,说,“那回,你就是这样抓出一只老家贼,你递到我眼前,我伸手去接。那是一只啥样的老家贼呀,可不一般呢。你自己没细看,我估摸,至少得有四五岁了,它那嘴,黑石头似的,黑硬黑硬的,和涂了蜡似的,闪着光呢。它那眼睛,黑小米粒似的,玻璃似的,刺人眼。它咋样叫,它这么叫,吱,啊,吱,啊,像吹号。那只老家贼,肯定是我们院里的家雀王,别的,全是它的臣民。把我欢喜的,都快背过气去了。可你,一松手,‘腾’, 放跑了。为啥呀?”
“为啥?还不是因为你两手空空。那天,你们几个,有拿糖球的,有拿烟卷的,只有你,啥也没拿,啥也不想给,空手就想得个老家贼呀。做梦吧。看见你想空手套白狼,我就把它放了。”老村长说。
“村长啊,你是不知道呀,”那个老沈头说,“那天,我真的没空手,我准备了一样东西,料你保准喜欢,只是我没像他们仨那样亮在手上。我那东西,不能往外亮,在兜里藏着呢。你不知道我藏了啥吧。那东西,少见,是我从我爹那儿偷来的。烟嘴儿,象牙的,象牙烟嘴儿。我怕他们看见告密,就藏着掖着,没露。预备躲开他们偷偷的给你————”
接着,他描摹起那支烟嘴来。我们想,这个老沈头不一般呢,和白沙梁的老头们不一样啊。他说话细切生动,极其夸张。在他的言语中,那支象牙烟嘴简直成了稀世珍宝。我们问他多少钱买来的,他的回答是“一百大洋”。我们又问一百大洋是多少钱,能买到什么。他想了半天,说,他也不知道一百大洋是多少钱,但他估摸,一百大洋,能买一辆“东方红”链轨拖拉机。
这句话把人们吓了一大跳。